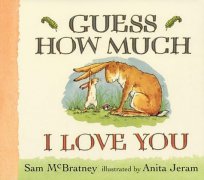贩夫风景
|
贩夫风景 只要是夏天,“豆腐花”的吆喝声便一路路炽炽烈烈要断不断的,坡下喊到坡顶,然后又一跌一宕的滚回去。那是个瘦瘦小小的中年人,黝黑的脸,老戴顶窄边草帽,大概喊惯了也就声如洪钟,一条线直冲七重天的高亢。每回见他总觉得真是少见的瘦,露在短裤下的腿干巴巴的,叭叭叭像鸭子的走步。 我们不常买,嫌麻烦!逢买必用家里的碗,怕他的脏,会得肝炎。暖烘烘盛满一碗往回端,往往以为盛着一窝云,阳光下笑得好开心的样子,真的难道不是,云竟在我手里呢,一朵开心的云。 他也卖肠粉,那是早上的生意,还有其他粉果白粥拉拉杂杂的,在这儿做开了,让警察拉过仍不肯走。有时候一个女的帮他,想是他女人,胖胖圆圆,两人并立简直点错鸳鸯谱似的滑稽。照理胖人爱笑,但她不笑,亦不说话,什么都听男的,男的凶凶的咧嘴骂,她只唯唯诺诺的应。不过她十分慷慨,分量作料都给得多。一回买肠粉,说要多点酱油,她提着酱油壶嘘嘘地浇,男的一把夺过来,开口便骂:“要死了你,给那么多……”女的不作声,亦不委屈,平静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看他们真好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流动雪糕车是浅鲜的绿,一汪一汪都是它耀眼的绿。远远便可听到它清脆玲珑的童话音乐,老是那几句,反而老是听不完。车子像那种上发条的玩具,发条上满了,车子一边行一边撒碎碎的音符,像一个流浪小孩的歌唱,唱自己的生涯,倾诉他多么欢喜的来,又多么欢喜的走。 雪糕车一停,四面八方的小孩子都围拢来,一人一杯冰淇淋高高兴兴地离去,而雪糕车是做完善事的卖艺人,慈蔼万分地瞧他们笑。太阳也陪着笑,一蹦一跳地热络,这下子冰淇淋一滴滴猛淌,小孩赶忙舔救,舌头伸得长长的;一滴沿臂弯溜,又忙着舔臂弯,就这么狼狈的舔去童年。 棉花糖不常来,来了安顿在对面大厦门口,挨近卖冰淇淋的,没事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卖冰淇淋的聊。他头发尽白了,蓄平头,一髭髭短椿子在脑勺上砌梅花椿,却有一张四十多岁的脸孔,怪怪的。他非常喜欢小孩,逗得他们咯咯的笑,更叫人想起童话里的善心老艺人,在街头做木偶戏给小孩们看。买棉花糖,一支空棒子绕着轮子转,轮子嗤嗤地吐丝,绕成一个头大的球,比小孩的头还大,粉红色,又是一朵天上的云霞。简直吃空气一般。幻灭之快的,咬一口,便没了,仅仅留下糖液在齿缝间。额上、鼻尖、下巴,沾得黏黏地。 糖炒栗子较远,得下好一段坡路。老远就听到炒栗子声,一铲铲尽是跳跳脱脱的冬阳,热辣辣的、香炽炽的。冬天在栗子香中竟也不冷了。 卖栗子的是个年轻小伙子,通常都赤着肩膊,大北风中也只一件单衣。人老老实实的,也不和谁搭讪,要多少给多少。我反而喜欢这样的交易,不言不笑中,自有人间情味。他是个有商业道德的,我吃遍那么多摊子的栗子,终归是他的好。栗子是太小的不好剥,太大的不香,中等偏小的最佳。就算外面有上等货,我亦回来才买,好像他这儿是我家乡。 我每经过必看见一碟闪蜡蜡的栗子,炒得爆烈了,里面的金黄作势要跃出来,可是壳儿始终欲吐还休,看到人愈发馋了,我至少得买三块钱,大银洋打在瓷碟上倾拎哼楞,是生意的直情直性。我也喜欢那盛栗子的长木桶,老让我想起韩国的长鼓,不定敲击起来也可伴歌成拍。那硕大的镬①〔镬(huò)〕锅。实在是丰富的矿藏,一粒粒棕色壳儿里都是金,而且镬边是个避冷的好地方。 (责任编辑: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