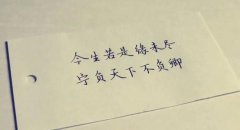不敢道别
|
2005年国庆节前夕,我和家人要迁移到十堰定居。这个人生大转移的大行动,是应了不满5岁的孙子陈植松好多次的强烈要求,他的爸爸同意并且做了主张,最后由他的奶奶我们这个家的铁杆当家人拍板敲定的。我这人向来随得方就得圆,只要一家老小乐意,我没有什么不乐意的。 正式搬家的吉日,是我自己旋转着一枚阳刻着天干地支的专用铜钱择定的: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公历9月29日)。为了一家人和送行的至亲一进新居就有家的感觉和舒适,我和“连襟”三哥提前三天就乘坐一辆便车,率先装了一车家具出发了—— 那一天,大雨纷纷,道路泥泞,车走完了明清梁子,我忍不住摇下了驾驶室玻璃,探出头来,一任雨水浇淋,我要把竹山城再一次远远眺望一回!啊,生我养我的竹山啊,难道我真的要和您道别了吗?但是,吃了55年竹山粮,饮了27年堵河水的我,面对古老而又全新的竹山县城不敢道别呀。俗话说,故土难离,故人难别。然而,我最后还是附和了家人的选择,对竹山做别离行。 大雨,哗啦哗啦地下,马达轰隆轰隆地响,雨声和马达声交织成一支使人脑袋胀满的惆怅曲。屈身俯首,双目微闭,回顾我在竹山成长的55年,说得上是悠怨与惬意夹杂,悲愤与喜悦并存。29岁以前,我是在县西部中心地带的宝丰镇度过的,在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家,由于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被判30年长刑,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毛旦”不会打、“铁环”不会滚、“房子”不会跳、毽子不会踢——不敢与所谓“根红苗正”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童年,度过了小学毕业考试与升学考试门门成绩都优秀街道书记却坚决不允许我上中学的悲愤恨怨的少年,度过了在街道建筑队多劳少得遭人白眼歧视的青年时代……我不服气命运的安排,不服气人世和世人的捉弄,为了寻找能够伸直腰杆、扬眉吐气的出路,我毅然捉笔,用工地上的水泥包纸写新闻写消息,进而操练文艺创作,四五年以后居然成了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 幸喜29岁那年(1979年)家运随着国运转,我被县里“特招”,偕妻携子迈向了竹山县城,来到了文化部门,干上了专业文艺创作,而且是主攻文艺形式中最难的剧本创作。虽然工资低微,毕竟成了国家干部,成了“革命同志”,还居然成为指点、辅导业余文艺创作的“老师”。 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异常勤奋地钻研文学艺术,终于成为湖北省戏剧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学会、楹联学会会员,我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和专业机构的认可和肯定。在1979至1997年的近20年中,我一直是工作上的模范、优秀、先进,与五届领导和同事的感情是鱼和水般的和谐,干起事情来,样样顺心顺手,左右逢源。 1997年至2001年这五年,因为敢与新局长顶牛,我这个二十年如一的模范优秀先进评不上了。县直机关的人都说我是楞头青,闹得满城风雨的。于是,领导关系、群众关系忽然一下子都“不好”了。 2002年以后的新局长上任,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和极大的工作热情,把我这个文艺股长该办的文化艺术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于是我又是连年模范优秀先进了!其实是在稍稍和谐一些的环境里,我恢复了我对待工作、事业的一惯态度,和做人处世的一惯风格与品质。 这几年,我确实学乖了,弄得局长越在人多的场合越说我是个宝。说是“宝”,有溢美之嫌,准确地说是“少”。因为全县三四十万人民中仅有我这一个人在主要从事演唱作品的创作,这4年来,我为县里的经济建设确实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紧密配合县委、政府中心工作创作了一大批文艺演唱节目。县委书记亲自安排为我买一把高级二胡,以作奖赏,组织部在提拔了许多小年轻以后也真心诚意提拔了我这个老家伙为副主任科员。 要离开竹山了,但是我不敢道别。因为我为竹山所做的贡献还不算太大。在走的前一天,我专门整理了一下歌颂竹山的演唱作品,也只有42万字的东西(其中大小剧本30部)。不敢道别,是因为我的党组织关系、工作、工资关系还在竹山,甚至户籍户口还是在竹山,先人的坟茔还在竹山。不敢道别,是因为人小面子窄无权无势,张扬了如果无人送行,那该几多尴尬?或许同事知道了为着送不送一份礼而犯难。俗话说得好,可以多欠一笔债,不可欠人一份情!如果竹山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打个电话,或者带一个甩手子信,我还是会回去帮忙的,希望竹山人见了我,说一声:“你回来了?!” 编辑点评: 作者搬家了,离开了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竹山县城,作者的情感是复杂的。文章回忆了作者家在这里经受的与国家命运相悲喜的经历,讲述了作者在竹山县的文艺术工作情况,在文艺工作中的欢乐和不痛快,这么丰富的经历,怎么能让作者不眷恋故乡呢?特别是文章结尾,用幽默的笔墨写内心的期待,把这种眷恋之情推向了最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