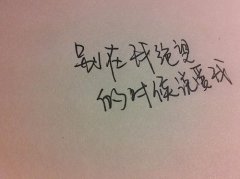儿时的过年
|
过年过年年年过,年年过年年年过。我喜欢过年,我怀恋那个过年,儿时的过年…… ——题记 想起几十年前俺那小时候,盼年总是数着手指头。临年近了,穿在身上的棉裤棉袄早已在炕席将膝盖和肘部的纯棉线布磨漏了,娘是缝了几缝,又补了几补。娘找出了头一年给俺做的又长又大的小花褂,试了试说:“还行,今年不恁大了,过年还能穿一年。”又让姐姐去买盒蛤蜊油,负责给我和小弟洗洗那皴裂的小黑手。姐买顺便回了一根红绒绳,喜滋滋地把我拉到她的跟前,把平时我留的灶坑门头发撮起一小绺,打了一个蝴蝶结,拿过镜子让我照一照,把我乐得与姐搂个亲,转身就像小燕子一样飞出了家门口,院子里的女孩们踢着盒子,男孩子打着冰尜,我扬着冻红的脸颊,故意把围巾围得低一些,露出二姐给我扎的那个蝴蝶结,寒风中那抹艳红,把喜庆红火的年味调得好浓好浓! 娘就喜欢男孩子,连买年画都要买上几张骑大鱼的白胖小子,她自己还编了一套顺口溜:“白胖小梳歪桃,连年有余乐陶陶!”这张年画贴在了细沙抹平的土墙上,平添了喜庆的过年气氛。娘用鸡毛掸子轻经地拂去了纸糊窗上的尘土,将一领新的术楷席铺在了炕上,拿出了只有过年才用的一块大花布单子,把全家人陈旧的几床粗布铺盖给罩上了,这屋里一下子便比平时亮堂了好多。 炉盖上烤上几个大红枣,放到暖壶里泡上一会儿,倒出一碗,顿时飘出丝丝缕缕的甜味儿,喝上一口,特别的清甜,直甜到心里头。爹买了挂小鞭拆下十几个给弟出去放两响,我拉着风箱白气黑烟在外屋弥漫着,娘和着面蒸出了一锅松软的全面馒头,又去切那带着冰碴从缸里捞出的绿盈盈的酸菜来,吃着白面馒头,就着酸菜,那味道香极了。 细细的酸菜丝儿,薄薄的五花肉,酸菜那个鲜哪!五花那个香哪!大猪头在锅里的开水中翻腾着,漂着平时少有的油珠珠儿,闻了又闻,嗅了又嗅,哈喇子都流了出来,我就一个劲地问娘锅里的肉啥时能熟,因为我和弟最小,熟了娘肯定得让我俩先尝上一口。 那时除了酸菜、白菜、土豆、萝卜外,冬天也没什么菜,平时就是咸菜酱。过年的时候,天气特别寒冷,家里大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很厚一层的冰,白菜萝卜也都冻起了泡。过年也只有吃酸菜馅水饺了,剁点猪肉,拿出只有年节才供应的精粉,一家人唠着嗑包着饺子,每人二块糖球,一把葵花籽,剩余的娘说好了,等过了年没客人来了再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听话,给啥吃啥,大人说的话,我们都会像圣旨一样无条件服从的。 葵花籽是凭户供应的,但秋天爹去大地捡的玉米还有,寻来家乡特有的白眼沙,在大锅一顿炒,用皂篱捞出来,酥酥脆脆苞米花就作为过年的小吃,娘还会炒些带咸淡味的黄豆,又香又脆。这黄豆不是随便管够吃的,每人只能分上一小把。因为太少了,我们自然舍不得一次给吃完,装在口袋里摩摩娑娑的,来到院子里的小朋友面前显摆。孩子们一个个都炫耀着各自的小吃,看着看着就开始互通有无了,我给她几个咸豆,她给我几个炒窝瓜籽,不多不少,一个换一个,拿到手中后,迫不及待地品尝着别家的新鲜小吃。 吴姨家孩子多,她家五丫跟我们的年龄相仿,但我们都不愿和她玩,因为她特馋,脸皮特厚,谁吃点啥东西她就伸手要,“给我点呗!”你要说她“管人要东西吃不嫌磕碜啊!”嘿,她眼睛一瞪伸手就抢。平时她像跟屁虫似的,见我们玩她就往跟前凑乎,我们那时虽然也不讲究卫生,可她比我们还脏,可能是穿得不暖和,常抿着清鼻涕,把两个绷着旧袜套的袄袖子头蹭个锃亮。为了她那个馋,抢别人的东西吃,她妈没少掐过她,最后她是不抢了,见人吃啥就回家磨叽她妈要,当妈的实在没辙了,只好给她在锅里贴上两个玉米饼子,熟了后她用筷子抹了一点黄酱,一只手拿一个,摇头晃脑地凑到我们跟前来吃,那股独特的香味扑鼻而来,直勾我们的馋虫呢。 过年真好,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才能向大人提点小要求,也无非是看谁家做啥好吃的啦,就回家求娘做点。娘呢,省了细了一年了,也尽量想着法子满足我们的要求。 油灯填满了油,平时再省再细,除夕之夜的灯也要点上大半宿,那时虽没什么电视看,也没什么好玩耍的,但每家五六个或七八个孩子进去出来,嘻嘻哈哈,你推我搡,喧喧嚷嚷,好不热闹。 “吃饺子喽!吃饺子喽!”小弟乐颠颠地爬上了炕,一家六口人围着热气腾腾的桌子,坐满了热炕头。虽然没有戏匣子听,但狭矮的小平房里其乐融融,充满了欢声笑语,全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中,吃着香喷喷的饺子,满心欢喜地守候着新一年的到来。 娘总说三十晚上灯要亮一宿才好,财神才会住这儿,所以娘总会拿个小碟用棉花捻个细细的小捻,倒点豆油放在外屋两家共用的厨房里,让它亮上一大宿。 过年真好,穿新衣,戴新帽,吃白馍,有菜肴,邻居见面都问好,时而一响小鞭炮,大人孩子喜洋洋,没有怨声和载道,唯一有个大心愿,那就是天天过年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