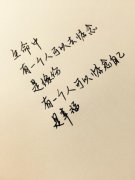奶奶的姻缘线
|
我摊开奶奶枯瘦的手掌,找寻她掌心里的姻缘线。那是一条细细的,若隐若现的纹路。奶奶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说:“娃,看啥呢。”我说:“奶,我找你的姻缘线呢。”奶奶无声地笑了,“哪有什么姻缘线,一辈子嫁给你爷,糊里糊涂就过来了。”这是奶奶生前,我们祖孙俩最爱开的玩笑。 我从小叫她奶奶,但她其实是我的姥姥。她一生没有儿子,生养大姨二姨和我妈三个女儿,院子里的人就说我是奶奶的外孙女,奶奶不高兴,什么外孙女内孙女,我娃就是我亲孙女,就叫奶奶!从此后,姥姥便成了奶奶。奶奶疼我,爷爷也疼我。奶奶今天上街给我买块巧克力,爷爷明天就买回几只蜡鸭子,但他们从不一起出门。我常羡慕隔壁的张五爷一家。我趴在窗户上,看见张五爷一手牵着五奶,一手牵着孙子出去玩,就问奶奶:“奶,五爷都拉着五奶和斌斌上街呢,你和爷爷啥时候带我上街?”奶奶皱眉低头纳鞋底,一言不发,我便不敢再追问。 后来才知道,奶奶与爷爷的婚姻是封建家庭媒妁之言的结果。奶奶是不识字的普通农村妇女,而爷爷是村里的高中生。爷爷的妈看中奶奶的贤惠和本份,定下这门婚事。但爷爷始终不爱奶奶,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爷爷独自进城谋生,新认识了女人,生下一个儿子。我曾问奶奶:“奶,为什么你不和我爷离婚呢?”奶奶惊讶而艰难地说:“那时候女人哪里做得了主,男人是家里的天,我一个农村妇女,离了婚,你两个姨不就饿死了?”我们一老一少坐在夕阳里,我看着奶奶干枯而布满皱纹的脸。多年后,我也成人,总忘不了奶奶脸上平静而复杂的表情。人常说,敢于舍弃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需要勇气,但更大的勇气,是敢于接纳和容忍。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她的心里,该有多少挣扎与隐忍。 爷爷和奶奶的话不多,人前人后,两人说话从不彼此称呼,直接白搭话。实在需要称呼时,就用“梅她妈,梅她爸”代替。梅是妈妈的名字。有一年,爷爷单位组织职工家属旅游,游览寒窑遗址。据说寒窑的主人是唐代宰相王允的女儿王宝钏,为了反抗封建婚姻争取自由,苦守寒窑十八年,等待丈夫归来。奶奶没文化,听不懂景区讲解员的讲解,她弄不清唐代究竟是啥朝代,宰相官有多大,只是听到讲解员说王宝钏等了十八年后,背着两只手,在王宝钏泥塑的雕像前,呆呆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她发了好一阵愣,扭头看我蹲在地上玩,问我:“你爷呢?”我爷和几个单位同事站在远处吸烟说话,并没有向这边张望。 回去的路上,路过一条又深又长的沟。张五爷拉着五奶的手走,对走在前面的爷爷说:“老周,拉着嫂子走啊,路陡。”爷爷停下来,等奶奶迈着小脚一步步走上来,嚅嚅嘴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奶奶看着爷爷,故意大声说:“没事,没多陡,我能走。”她不知是想化解爷爷的尴尬,还是自己的尴尬。两人一前一后走着,我人小走在中间,长长一段路,爷爷有时和同事说几句话,有时和我说话,他们两人,始终没有拉过手。 我有时恶作剧地心里想,盼望他们吵架,吵架了我就能看热闹。可他俩从不吵嘴,说到火药最浓处,总有一个人先闭了嘴。但人和冬天里的热水袋一样,水存得太满,终究是要爆开,一旦爆开,就带来巨大的伤害。上小学五年级时,爷爷不知因什么事和奶奶吵起来,生了很大的气,重重摔门而去,说再也不回来了。奶奶一下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家里静得可怕,我从未见过奶奶哭得如此伤心,她的鼻涕和眼泪落在衣服上,地上。我吓得躲在一边,奶奶对妈妈说:“梅,去把你爸找回来,他年纪大了,不敢生这么大的气……” 我躲在屋里,看一直坐在地上的奶奶。她忽然间变了一个人,空荡荡的屋子里,地上是一个无助的白发苍苍的衰老女人。奶奶可怜的样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多少年后,我常想,她是最老实、最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虽然生于“五四”运动那一年,却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半点熏陶,她不懂得独立,也不懂得反抗,她只是愚笨而朴素地知道,嫁给这个男人,就是把命给他了,要过一辈子。 年一过初八,家里亲戚都走过后,爷爷的儿子就来了。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给爷爷的,也有给奶奶的,但他从不称呼奶奶,和爷爷一样白搭话。他是爷爷当年和外面女人生的儿子。虽没有一起生活,但爷爷一直资助他上学。奶奶待他如亲生儿子。每次来,必有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奶奶那天必定早早起来,妈妈买菜准备,她们总是笑,好像真有什么喜事似的。年幼的我看见她们笑,也觉得喜庆,竟暗暗盼着我那“舅舅”来。那天,平时很少说笑的爷爷忽然变得话多,嘴不停地笑,一家人吃饭也和和气气,“舅舅”临走时,奶奶还要送出大门,叮嘱天黑路上小心。送走了“舅舅”,爷爷回屋睡觉了,奶奶默默收拾桌上的碗碟,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大家也不问,收拾完各自睡去。每年的那一夜都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我那时小,只看见奶奶笑,如今我也结婚成家,想想那一夜里,奶奶该有多大的委屈吞咽在肚里,又或许一夜无眠……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在某个夜晚等待老公下班时,常想起小时候我陪着奶奶坐在小小的屋子里,等一家人下班回家的情景。晚上爷爷下班后,吃完饭就出门打牌了。寂静的夜里,奶奶舍不得开灯,坐在黑黑的屋子里陪我看电视。电视机一闪一闪的光照在光秃秃的墙上,我看得兴高采烈,奶奶却常常看不懂电视里演什么,坐在我身边,就着那一点微弱的光,缝补衣裳,剥绿豆皮…… 奶奶临去世那几年,已经卧病在床不能下地走路了。爷爷也中风躺在床上。他们两人一人一间屋子分开躺着,每天听得见彼此的声音,却不再见面。病倒的奶奶再也不能给爷爷做饭,一次姨从外地赶来看她,在家做饭,饭做好了,奶奶挣扎着坐起来指着碗柜第一层对姨说,你常不在家不知道,你爸有他自己固定的碗呢,他吃饭不回碗,给他盛满。 我们都回过头来,看着床上这个瘦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她说完安详地闭上眼睛躺下了,安静地如一泓湖水,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