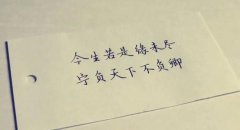记忆犹在
|
我跟老妈说想去从前的小学看看时,是我有事回老家正和妈妈坐在院子里聊天。院门外,老妈的菜园子里一架一架的豆角长势喜人,白边紫蕊的豆角花在绿色的叶子间探头探脑,艳黄色的冬瓜花趴在胖胖的冬瓜上偷偷地四处张望。 老妈听着笑道,有什么好看的,好久没有人收拾破破烂烂的,都长满荒草了。我知道小学校里早已没了学生,老师们已经被分流到别的学校了,而村里的孩子不是去了镇上的学校就读就是被他们的父母送进了城里的学校。离家二十多年,“没了”或者“破破烂烂”在我的乡村时时上演,人渐稀少,物非人非,一切都不是昔日的模样了。 但是,我还是迈步出了院门,向村西走去。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边,门前有一座桥,桥下这条河的河水向东流进了洪泽湖,这条河常年不干涸,夏天可以在河里洗澡也可以摸鱼捉虾,冬天河面结冰,我们可以在河面溜冰玩。跨过桥是横贯村子的一条不宽的路,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不到两里地便是我的小学了。以前,这条路是泥路,每到下雨天,泥搅着水,泥泞难行,放学回到家,妈妈都会抱怨我们一个两个成了泥猴子,如今,这条路已经在几年前镇政府出钱铺成了平整的混凝土路面了。 向西走上一段路,路的南北两边都住着人家一幢挨着一幢,基本上都是红砖红瓦的房子,有的带着院子,有的人家不带院子,就是三间正房带着偏房。几乎无一例外,每幢房子前都有一个不太大的菜园子,记得那时候到了夏天菜园子里种着葱、蒜、韭菜什么的,村民们在田里干活回家迟了来不及买菜就在自家的菜地随手摘几条黄瓜,一大把长豆角,只需一会功夫,桌子上便摆上了卖相很好的几盘菜。 再往前走一点,路的南边是村舍北边就是一块连着一块平平整整的农田了。每到春天,田埂上长着各色的野花野菜,也有一两棵野杏或者野梨树夹杂齐间,野树上开满了白的粉的花儿,惹的蜂飞蝶舞,我们上学放学一路玩一路走,捉蝴蝶摘野花,笑声阵阵伴着长长的日影儿。 上下学的路上有时会遇上下雨,那也不用怕,随便哪家屋檐下都可以躲雨。屋里有人在的话会喊我们到屋里去躲雨,基本是不进去的,有的爱开玩笑的叔叔婶子就故意大着嗓门问,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拗?记得是小学二年级吧,我被问气了,便冲了人家一句,你家的。人家站在家门口大笑起来。以后每次路上遇到了我,离得老远就会逗我,我家的孩子,快跟我回家去。于是我便羞红了脸,再遇上便躲着得远远地走。 走近学校,远远便看到学校矮矮的围墙还在,深灰色的大门也在,走近前看大门上锈迹斑斑,没有上锁,我推开虚掩的大门,迈步走了进去。校园里杂草深深,两排门朝南的红砖瓦房一前一后在夕阳中静默无语。记得当时村里多数人家还是茅草屋,我们小学的教室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了。如今年久失修,已经斑驳的不像样子了,在房顶上有一株野草正在风中招摇着绿色的身子。校园的东南角,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池塘很浅,池塘边立着柱子,防止学生进池塘的。池塘里被那位姓杨的女老师放上了莲藕,每年到了夏季,几朵白色粉色的荷花,亭亭地立在碧绿的荷叶间,一校园里都弥漫着荷香。现在池塘没了,地面早已被整的平整,上面被杂草覆盖。在校园的后面靠近围墙有一排白杨树,现在异常高大,不知谁家的一群鸡鸭正在树下四处觅食,一边叽叽咕咕地说着它们才能听得懂的话。 在学校大门的西边曾经有一颗大大的柳树,上面挂着一个铁钟,铁钟敲起来时声音传的很远,当上课的铃响起时有孩子从家里奔跑过来窜进教室,而下课铃声慢悠悠地不急不躁地敲起来时,一群孩子便如一只只小鸟一样,飞出了校门。有一年春天,记得柳树根抽出嫩绿的柳芽儿,有一个男生趁老师不备,爬上树去,掰下几根柳枝圈成了一个圈当成帽子戴在头上,另外两个男生来抢,于是几个同学打闹在一起,女同学躲在一旁看热闹,刚巧被任课老师逮个正着,于是那几个同学被罚站着听了一节课,如今,那嬉闹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大柳树却不见了足迹。 想一想那时候的老师也有趣的很,他们多数是家住本村的。走进教师室时,他们教我们识字,出了教室,他们也成了农民。到了星期天节假日我跟随大人们下田,经常会遇到我的老师,他们也会打着一双赤脚,肩膀上扛着锄头,或者手握一把镰刀,有的担着两袋肥料,他们这是下田干农活的。那时候的我真的很腼腆,每次遇到老师,都会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小声地打个招呼后匆匆走开,倒是老师们都笑嘻嘻的,不像在课堂上那么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 我一边顺着记忆想着,一边沿着围墙走着。 这时有人走进了校园,老远就大声问我,回来看看的吧? 我回答,是的。 前几天我来赶咱家的鸭子,也碰到了有人来,是夫妻俩,还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认得好像是前村有德三叔家的玉蓉,她说是从上海回来,我看她拿着手机一个劲地拍照片呢。 是吗?我笑了,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沧海桑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在我的心里有这个小学的位置,在我散落天涯的儿时的玩伴心里也有关于它的记忆在,我们的灵魂回归,终究还是有迹可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