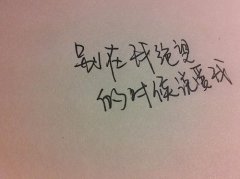娘在天堂
|
一 我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到二年级了,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还不会做,被老师送回家。正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地做衣服的娘,眼帘低垂着,视线没有离开上下飞速窜缝的针头,问道:我这儿子会不会留级? 留级是肯定的,如果是低能儿的话,是要退学的。 低能儿?缝纫机停止了欢唱,娘将针头下的两片布的布边拉伸贴紧,缝纫机又嗒嗒嗒地唱开了。娘说,不会吧? 老师看了一眼傻傻站在一边的我说:二位数的除法,全班五十个学生都是一教就会的,就他教牛一样,一遍一遍教不会,不信你看看他今天做的作业。 娘这才抬眼瞧了一眼老师,停下手头的活,打开我的书包,翻开我的作业本。本上只抄写了几个例题,没有计算过程,也没有答案。娘说,我这儿子我了解,还不至于痴傻,主要是胆小,不懂的地方不敢问老师,在家里我教教他,用不了几天,他会赶上来的。 两天后再上算术课,我惊喜地发现做二位数的除法,竟是这么简单而有趣。老师看了我的作业本,把我叫到黑板前,重新出了一道题,要我当场做给她看。我把计算过程和答案写在了黑板上。老师瞪直了眼睛:前两天对着算术题还懵懵懂懂的呆子,怎么突然会做算术题了呢? 我知道,这完全是娘在家里教的结果。 二 娘能够教我算术,说明娘是上过学的,但我之前并不知道,娘对我兄弟几个也从不提起。 娘不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会上山下地干粗活,会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会参加社队的批斗地主大会和忆苦思甜大会。娘很少出门,很少走亲戚,连供销社、收购站、卫生院这样的公共场合,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基本上呆在家里,除了做家务之外就是裁剪布料做衣服。本村和周边村的乡亲送来的布料在裁剪台的一角叠着,娘日日夜夜裁来缝去总不见少。我没有办法将孱弱的娘与上学识字的文化人联系起来。一次,我做完家庭作业,趴在娘的对面看她缝纫衣服,问:娘,您上过学吗? 上过学的,娘读了六年私塾,起码相当于高小毕业。 高小毕业,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就读的大队小学里有五个老师,除了两个年轻老师是高中毕业之外,另三个都是高小学历。我说:做老师比做裁缝有出息啊,娘为什么不去学校做老师呢?我也好沾娘的光。 老师哪有自己想做就做的?娘踩着缝纫机说,不要管娘,娘只想你兄弟几个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当老师,能有出息。 大队小学毕业了还要不要上学? 当然要上学,到公社去上初中。 那公社初中毕业了呢? 上高中呀,你兄弟几个都要上高中呀。 那时候,大队有小学,公社有初中,而高中,要到二十多里以外的区上去上的,要带粮带铺盖住校的。我问:家里供得起吗? 只要娘还能做衣服,就是拚了命,也要把你兄弟几个,一个一个供去上学。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上大学这回事,以为高中毕业就到顶了。我问:那高中毕业了就能当老师,就有出息了是吧? 还不行,还要继续上学。 那,到哪里去上学呢? 娘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的踩缝纫机。缝纫机嗒嗒嗒地唱着,似在替娘说话,但是,唱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呀。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我不知道有上大学这回事,娘却是知道的,那时候的大学叫工农兵大学,只有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通过大队、公社、区、县层层推荐上去才能上,而我及我的兄弟注定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叫娘怎么回答呢? 娘将衣服缝纫好,举起来检查了一番,就开始一针一线地钉钮扣。娘又说:不能继续上学就不好好读书了?不可作贱自己呀,学到的知识是别人拿不去的,回生产队种地照样用得上。 那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首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打油诗,我记得是这样写的: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讨饭;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学了这一课文,我头脑里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在旧社会,凡是贫下中农都是逃荒要饭的,只有地主才上得起学。因此,区分好人与坏人非常简单,凡是文盲就是贫下中农,就是好人,凡是识字有文化的就是地主,就是坏人。爹是文盲,所以是好人。娘呢,比爹年长很多,肯定是在旧社会上的学。哎哟,坏了坏了,难道娘是地主?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现实,我又用反推法驳斥自己:如果娘是地主,公社、大队甚至我就读的大队小学,经常开批斗地主大会,怎么不见娘被押上台批斗过?如果娘是地主,那外公和大舅肯定也是地主,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不好说,大舅就在本村,却是贫农。我想来想去,头都想疼也没有结果,就嚅嚅嗫嗫地问:娘,您会不会是地主? 娘似乎手被针扎了一下,突然停顿了手脚,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埋下头继续钉钮扣了。 娘终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第二年冬季得了一场暴病,竟去了另一个世界。 三 娘没了,偏偏爹又患了肾病。爹是木工,做不了重体力活了。奶奶本是和爷爷住在山上老屋里单独另过的,住到我家来了,养鸡、喂猪、洗衣、熬药、做饭……撑起一个残破之家。上初中的哥哥辍学了,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壮劳力一个工记十分,哥哥记三分。我和弟弟仍然上着学,放学之后要去拨猪草,要给自留地除草;农忙时节要帮忙收割庄稼;寒暑假里,主要是跟随大人上山砍柴。 爹的肾病渐渐好转,复工了。 日子流淌着,苦涩,艰难,也不乏希望。 由于连年的“农业学大寨”,近处的山都被糟蹋得光秃秃的,砍柴要到外大队的深山里去才行。早上太阳还没出山,带上准备好的中饭出发,走二十多里山路到了外大队的深山,将中饭存放在就近的山民家里或山铺(看护山林的人搭的简易草棚)里,砍好柴禾去山民家里或山铺里歇脚吃中饭,再挑着柴禾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人也累成一摊泥了。 有一次,我跟随邻居大哥进深山砍柴,在山铺里歇脚吃饭。山铺的主人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爷爷,问起我是哪家的孩子。邻居大哥报出我爹的名字,老爷爷说不太想得起,我又报出我娘的名字,老爷爷立刻凑过来问道:你就是贞香(我娘的名字)的儿子?啊呀呀,第二个儿子也长这么大了。老爷爷告诉我,我外公本是苦出身,从江西那边逃荒到这,靠在这一带背毛竹开纸作坊,置办了几十亩田产,土改时定为地主。 既然外公是地主,那么我娘出生于地主家庭也就得到了证实。但是,娘的哥哥即我的大舅却是贫农,就住本村的东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爷爷告诉我,我的大舅也是地主,土改时集中关押在农会里。就在要枪决地主的前一天夜里,农会里有人趁黑夜打开牢门的锁,放跑了大舅和另一个地主,大舅从此踏上了隐姓埋名的逃亡之路,等到暴露身份从外地抓回来,五年时间过去了,不再枪毙地主了,改为发配到东北某农场劳动改造。随后,舅妈和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表哥)也被发配到劳改农场落户。老爷爷还告诉我,本村的那个贫农大舅和我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学校里老师讲革命故事,讲到过本乡两个地主逃跑又抓回来,我以为这故事与我家毫不相干,还和同学们一起鼓掌呢。啊,我娘在亲哥哥逃亡的情况下,认一个贫农作为干哥哥,后来又嫁一个贫农的我爹,这是活命的根本啊。 还好,我娘没有挨批斗。我这样说。 怎么没有挨批斗呢?老爷爷叹息一声,告诉我实情:大舅逃亡之后,外婆经受不住抄没家产和独子失踪的打击,忧郁成疾,两年后病逝。我娘是个老姑娘,到了三十五岁才嫁给我爹,出嫁的时候带着两大件:一是赖以自食其力的缝纫机,二是无依无靠的地主外公。那年,我哥在娘手上抱着,我还没有出生,有人要绑外公去游街,那是下着雪的冬天啊,娘把外公拦下,把怀里的我哥往奶奶手上一塞,就替外公让人绑去游街了。娘是在外公去世之后,三十九岁才生下我,过了四十才生育弟妹的。 不知不觉,我已经泪流满面。 老爷爷说:你大舅逃亡之后,你娘给你外公外婆养老送终,再把你兄弟几个带大,真是不容易啊! 四 娘之所以要对我及我的兄弟隐瞒身世,是因为担心我们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更担心我们自暴自弃,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结束之后,家庭成份问题就不是升学和参军的障碍了,我上初中,升高中,参军,读军校,入党,提干……似乎有神灵相助,一路顺畅。 记得奶奶曾经说过,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大舅,只要还在人世间活着,总有一天,会从遥远的北大荒回到故乡来看我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舅果真回来了,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大舅已近七十岁,摘掉了地主和劳改犯两顶帽子,是农业部直属的国营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的退休教师。大舅在外公外婆的坟前祭拜之后,在我娘的坟前呜咽恸哭,长跪不起。那时,我正在军校里学习,哥哥在书信上告诉我这一切。我想,娘在天堂,会听到大舅声声叩谢的。 回乡探亲的时候,爹对我说,你有今天的前程,该是**风水应验到你身上了。我不认为这是迷信。我拜倒在娘的坟前。伴随着香烟袅娜纸灰飞扬,我的耳边竟又响起了嗒嗒嗒的缝纫机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紧凑、时而舒缓,如歌如箫,如泣如诉。娘啊,这是您在说话吗?是的,是您在说话。家族遭遇劫难,身心经受重创,您有满腔的冤屈要申诉。命运多舛而抗争不休,日日操劳,勤俭持家,您有美好的愿望要表达。中年生育儿女,对儿女疼爱有加,同时也寄予了重望,您有太多的教诲要叮嘱呀。娘啊,您当年其实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不争气、不懂事的儿子没有听进去,现在您就尽情说吧。 娘啊,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