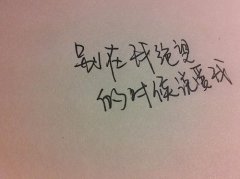甑子饭
|
截一段岁月的烟火,打开是百味的人生。 ——题记 一 民以食为天,炊具自然也日新月异。现今虽然有智能电饭锅或高压电饭煲做饭,方便了不少,但我更留恋木甑子蒸的饭,有一种独特的、淡淡的岁月沉香揉杂于其中。 小时候想吃甑子饭几乎是一种奢望,只有逢别人家婚丧嫁娶,或哪家大摆寿宴时才能吃到。 因为那时农村土地才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很低。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种地亩产三百斤靠力气,五百斤靠肥料,八百斤靠科技”。那时亩产大概也就五百斤左右,除去给爷爷的细粮,能剩下的米粮就很少了,父亲母亲做饭时常搭配一样粗粮,这样一年的口粮才能接拢。 那时我们并不懂经济的拮据,捉襟见肘的日子常有,可我们总盼望着吃席。既使在那个年代,我们老家也有一种风俗,无论哪家过寿或娶儿媳,都会有十大碗的宴席,炒菜在外。大锅大灶,置上木材旺火,几个小时的云蒸雾绕,到现在想来,那种香气也令人口水直流。竹蒸笼特有的淡香和蒸菜的香料在这水深火热中升腾、环绕,早巳融为一体,一阵风吹,香气扑鼻。而宴席做饭的炊具是木甑子,几十桌的宴席一个大木甑子蒸出来的饭也够吃了。 做甑子的材料有椿芽木和柏木两种之分,椿芽木做的甄子香味更浓一些,既使在各种佐料炒出的美味佳肴面前,它也不会失香。而柏木甑子香气很淡,但经久耐用。 木甑子上大下小,全采用立板钻孔串连而成,不会用胶水黏合,用两道至三道篾箍即可,让木甑子在碰撞的情况下也不会散形。篾箍是选隔年青的毛竹制作,这样的篾条更有韧劲。里面的篾搭子作工更考究,篾条需经过蒸煮,经过热胀冷缩处理,再过云刀去其棱角,然后编出的搭子,饭粒也不粘底了。 那时做席大多数都用椿芽木的,只因香气袭人,也许,正如闻香识人之故吧。大口大吃肉,大碗大碗喝酒。最后再盛下一碗香喷喷的米饭,那种惬意自然无以言表。 二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日子开始有所好转,家庭副业使家里焕发出了新的荣光,父亲请木匠到家里做了一口小木甑,我自然高兴得手舞足蹈。 甑子是柏木做的,父亲说经久耐用,当时我还是不能理解父亲为何不用椿芽木作,因为那种更香呀?父亲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识其表而不知其内,谁解其淡?” 我觉得爱看古书的爷爷也不会这样跟我说,因为他会把事物的原理阐述得很清楚。故,我当时对父亲的作法也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 母亲遗传了外公的基因,做得一手好菜,因为外公在当村支部书记之前,就是附近有名的厨子,母亲从小耳濡目染,也学到了不少。有了甑子,母亲在蒸饭时偶儿也会蒸上一两道我爱吃的蒸菜,譬如烧白(梅菜扣肉)、夹沙肉、粉蒸肉等。甄子蒸出的饭一粒是一粒,不像其它锅作的饭,要么很黏,要么很硬,甑子饭适合作蛋炒,当每一粒米饭都裹上了蛋汁,生姜、小葱入锅,加上些许盐,一盘炒饭就大功告成了。你可以再在旁边放上一碗米汤,因为米的营养成份很多在米汤里,时不时喝上一口,自然沁入心脾。但更多的日子是素菜相守,母亲会把一道看似极其平常的素菜作到极致。譬如凉拌三丝、凉拌折耳根、小葱拌豆腐。有这些菜垫饭,也不亚于吃肉的日子。 有些味道也许要到一定的年龄方可明白。自从我远离故乡后,我对甄子饭的思念与日俱增,或许那里有故乡的味道,家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而立之年,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故里,让母亲给我作了一次甑子饭。我不让母亲炒肉,炒了几道素菜,不加任何佐料,只放油盐。或年受素食者的影响,我之前也有过体验,当没有佐料后,菜根自然的清香味就出来了,我只是还没体验过木甄子饭与素菜的绝配。 当母亲把蒸好的米饭盛上,菜一一上齐时,我没有急欲动筷子。微微闭上了双眼,那种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云水之气带着柏木的淡淡香味萦绕于鼻间,菜根香缕缕如烟,此感觉让身子一下变得轻了,感觉徐徐升起,尤如登仙之境。 睁眼,饭还是饭,菜还是菜,我恍然大悟,对于父亲那句话的含义似乎明白了不少。人生太多的粉饰和欲望掩盖了生活的本真,故,难知其真,难闻其味。人生,更多是平平淡淡,一本书,一杯茶,一箪食,一瓢饮,又何陋之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