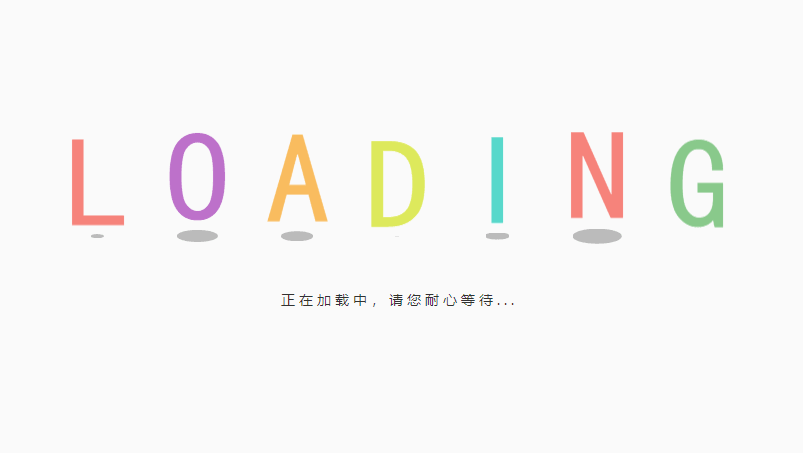世界上最早的毒气战 1915年伊普雷毒气战
|
世界上最早的毒气战是什么时候?1915年4月22日德国在伊普雷和附近村庄使用毒气进攻,称为伊普雷毒气战。下面就跟放肆吧一起具体看看世界上最早的毒气战等相关内容。
世界上最早的毒气战 自1914年晚秋以来,西线变得沉静起来了,尤其是比利时的佛兰德省,企图突破的顽强的德军不断被击退。进展都以码计,往往在又一次凶猛的小战斗中被夺回。在这个防区中,有一座古老的有护城河的城镇伊普雷,它位于形成十七英里纵深突出部的一条协约国战线后面,这条战线从斯唐斯特拉特西北五英里开始,弯曲地绕到伊普雷南面约三英里的圣埃卢瓦。炮轰几乎摧毁了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性大教堂伊普雷的克洛思会堂,但德军为这一行动辩护说,这些建筑物的塔楼被用作观察哨。
双方所用战术基本上受到佛兰德地形的制约,德军认为这种地形“不利于从东到西的进攻”。低洼地被半圈丘陵所破坏。在伊普雷西南山脊上五百英尺高的康默尔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如果德军能够攻占这个阵地,这座城镇就将陷落。山脊为火炮集中射击提供了观察和置放场所,可以轻易地使炮群不被在较低地方的守军所看见,同时增援部队和补给从后面运上来又不会被敌人看到。 8月中旬,一个加拿大旅开到伊普雷突出部,使法国人得到非常需要的休整,在加拿大军看来,法国的堑壕工事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长长的堑壕没有护墙为纵射炮火提供防御。在低地区域,地下高水位使掘到两英尺以上就不能再掘下去了,还迫切需要把胸墙用沙袋或泥土堆高到四英尺或者更高些。那些法军筑的胸墙,其厚度不足以抵挡子弹,有些堑壕连这种薄弱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没有一条战壕有防护来自后面炮火的背墙。 法国的士气还从卫生设施中反映出来,据加拿大官方历史宣称,这些设施都“处于可悲和非常污秽的状况,所有下面塌陷的小堑壕,都用来作为公共厕所和埋葬尸体的地方……他们后面的堑壕和地面,都乱扔着死人,有的已埋葬,有的未埋葬,许多浅葬的坟墓严重妨碍着挖壕”。 不久,胸墙都加高和加厚了。在有可能的地方,加拿大军就加深现有的堑壕,还开辟护墙和新的交通壕。所有堑壕都互相沟通,人们可以走到任何防区去,不致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连续的有刺铁丝网,保卫着整个系统。 在加拿大军调来防守伊普雷的同时,按照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的命令,奥—德军队集中在加利西亚,“永远消灭俄国人的进攻力量”。为了转移协约国可能的怀疑,他命令西线德军进行各种活动,结合“留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兵力所能发起的进攻”。这种性质的方案并不含有实质性的前进,而是试验新计谋或新武器的绝好机会。德国军史记载,“在4月22日开始的伊普雷之战,德国方面的起因是想在前线充分试验毒气这一种新武器。” 1915年4月22日是晴朗温暖的星期四,但在伊普雷突出部很不宁静。前三天,从可畏的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发射的一吨重高爆炮弹,已把周围土地打得天摇地动。德国在伊普雷和附近村庄的目标,大部分是非军事性的:街道、公路和桥梁被选为目标,但威力强大的炮弹也摧毁了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和生命。炮击区域主要在伊普雷的北面和东面。平静阶段从早晨晚些时候到下午4时结束,那时起这座城镇北面的法国防区受到猛烈的轰击,弹幕再徐徐移到加拿大军前线。 九十分钟后,炮击停止了。在朗热马尔克和伊泽运河之间的阿尔及利亚狙击兵和非洲轻步兵,注意到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绿黄色的云徐徐地向他们袭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片云飘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开始窒息,痛苦地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倒下来,闷死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好像被酸性物质烧灼似的感到烫痛。有一百六十多吨氯气,从德国堑壕特置的圆筒里放了出来。这种毒气差不多比空气重三倍,它乘轻微的东北风,沿地面滚滚而来,坠入堑壕。当英国部队看到发出尖叫声的幸存者抓住喉咙,盲目地四散奔跑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武器。但受到毒气窒息而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加拿大军,顽强地保住了这条战线。受毒气袭击的法军留下了四英里半没有防卫的缺口,但德军前进了两英里就停住了,等待毒气飘过去。法尔肯海因断言,及早开始毒气进攻,比突破敌人战线前进更为重要。 那天深夜,加拿大军狂热地工作着,填补这个缺口,并把火炮拉进阵地,德军照明弹照亮了夜空,使他们暴露于炮火之下。尽管还有氯气的余迹,加拿大军把他们的左侧翼延伸到法国防区,构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一等兵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建立了高度英雄主义的功绩,他带了一挺机枪一步步地前进,阻住敌人。他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英国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要是德军沿着这个没有防卫的缺口前进,他们就可以把伊普雷突出部分割开来,包围五万英国和加拿大部队。 德军使用毒气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尽管协约国固执地漠视警告。法军前一个月俘获的俘虏,就提到毒气筒,但不知道所用化学品的类型。这个情报刊登在3月30日于皮卡迪印行的《法国第十集团军新闻简报》上,但是法国指挥官没有采取行动。4月13日,一名德国逃兵向朗热马尔克附近的法国第十一师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两天后,法国第五军经过师一级下达到营一级的《情报摘要》报道,“俘虏所说的装有窒息性毒气的管子,已经放在炮群中,沿前线每四十公尺有二十管。”他拿出发给这种装置操作者的一个简单防毒面具,给俘获者看。 一个从敌人战线后方回来的比利时间谍宣称,德军将用毒气进攻,但他既不知道毒气的名称,也不知道使用的日期。比利时陆军新闻简报报道,德军在根特的一份高度优先的命令,要准备二万个防毒面具,以“保护士兵不受窒息性毒气的影响”,但这种毒气的名称不知道。这个报道还明确指出德军的进攻位置恰恰就是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个地方。 但只有一个人——指挥第十一师的费里将军——相信这个危险是真的,并把他的关心转达给邻近的英国指挥官们。费里还通知了他的上级,他的军指挥官带了一名从法国司令部来的联络军官来访问他。费里因为他没有经过霞飞司令部的正式渠道,而擅自直接向英军提出警告而受到申斥。他建议炮击德国堑壕以减少毒气进攻的危险,却遭到拒绝,并奉命要祛除他心里的非非之想。(后来费里被撤销了指挥权,就是因为他是正确的。) 最后的警告来自德军本身,他们在4月17日的无线电广播中谴责英国人说,“昨天在伊普雷东面,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的炮弹和**。”在采取任何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报复作辩护。 英国人为侦查警告的证据作了草草的尝试,但对德军堑壕的空中侦察一无所得,圆筒伪装得很好。英军指挥官休伯特·普卢默将军爵士,怀疑德国人是否会采取这种不义的行动,他只是把这种“姑妄听之”的警告转达给他的部下,而对这个问题置之度外。 4月24日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被加拿大军挫败,他们认出略呈绿黄色的气体正在向他们徐徐飘来。但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毒气的效力,就认为最初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但他们却不适当地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 匆忙地临时准备的防毒面具发给了士兵,但是由于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与此同时,一位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正在摸清敌人这个使人惊骇的武器。吕西托伪装成德国的旅行推销员,进入莱茵兰去获取德国**生产的报道。克虏伯在埃森和曼海姆的巨大工厂是最严格保密的。在曼海姆,这位情报人员看不到有毒气压缩在大小合适的圆筒中运往前线,但铁路油槽车正在向东北方向驶去。 吕西托不久就知道这些车辆开往何地和为什么要开去。他向地图一瞥,就知道油槽车是开往埃森的。这位情报人员装成一个出入于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的人。他很善于**,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转而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吕西托结识了克虏伯工厂的一位孤独的老警卫,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的耐心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这个警卫不久就谈到一次确实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这个特务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提议按一笔吸引人的赌注打赌。这位工厂警卫为赢得二千马克,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邀请他一起去亲眼日睹一次实际的军事演习区的实验。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引人注意,但可清楚地看到实验场的地方。载运德皇威廉和军政高级官员的一长列汽车停了下来。军乐队演奏军事歌曲,同时一支仪仗队举枪致敬。 一门巨大的海军炮和一门三英寸炮作好表演的准备,在将近一英里外山丘上一群在吃草的绵羊就是目标。野战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时声音较轻,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爆炸。几秒钟内,海军炮射击了。每个炮弹都没有向羊群瞄准,但每次爆炸后,有一阵略呈绿黄色的云状毒气徐徐升起,向羊群飘去,象低低地移动的雾一样覆盖在它们的身上。在雾散开后,所有绵羊都死了,集合的人群也走了。 几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巴黎实验室里,他的分析应能使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来,然而早期的防毒面具都不起作用。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废棉花。另一种防毒面具是“救火帽”式的,就是一个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 在协约国手中,有逃兵供给的虽然简单但较有效的德国防毒面具,但他们在从事毫无价值的设计中却不加以利用。当步兵在了解到没有有效的防护物可用时,他们对毒气的恐惧加剧了。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报道,“毒气是个可怕东西,没有人相信防毒面具的功效。……标着‘紧急’字样的粉红色军队打印信件,不断从司令部寄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防毒面具。信件都是前后矛盾的。最初说防毒面具都要浸湿,后来又说要保持干燥,然后规定要把它们放在小背包里,随又规定不要用小背包。”到了仲夏,研制了一种改进的防毒面具,但直到1915年11月,协约国才得知敌人怎样做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15年1月对俄国人发射毒气炮弹的效果微不足道,使德国人感到失望,在埃森试验的那些毒气炮弹是新型的。乘风向的毒气进攻后来被放弃了: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不久,固定的圆筒被毒气炮弹取代,这种炮弹可以打进敌人的防线,使部队没有时间来躲避这致命的雾。这种炮弹的**装得少些,以便为液体毒气留出空间,而在爆炸时液体就变为气体。 炮弹设计得可从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发射,少装**的炮弹把射程限制在五英里左右。这种炮弹飞行时不稳定地旋转,爆炸时声音较轻,是容易辨认的。后来德国人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协约国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但德国人保持了主动权。1917年7月,他们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大战期间,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德国炮弹都充了毒气。双方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德国对于泄露了即将进行毒气进攻的那个逃兵,是决不饶恕的。第十一师的前指挥官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轻率地提到他的名字。根据这个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判处他监禁十年。他是不可能恢复自由的,因为,1933年1月,纳粹掌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