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半生
|
她说当我在母亲的床上醒来的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院子里的太阳晒得正温暖,海棠花倚着墙角绽放出大片花瓣,她躺在木制的椅子上看着天空,湛蓝色的天空和云朵混合在一起,在她眼前慢慢晕染开来,她沉浸在那样自由而荒芜的世界里,过了她急促且短暂的三年岁月。后来她回忆起那三年的时光,她几乎想不起一丝一毫关于那段岁月里的记忆,直到后来也只剩下那片天空和云朵,角落里盛放的花朵、白色的兔子、滴着水的衣服、电视机里播放着樱桃小丸子动画片,母亲的白色印花被单和她居住的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她说房间是母亲的卧室隔开来的,洁白厚重的墙壁,一个白色的书柜连着一个小小的衣柜,她的床是1.5米略小的双人床,紫色粉色红色的床单交替,白色小狗乐乐就窝在她的床单上,呼呼的睡着。 岁月眨眼呼啸而过,白色印花床单变成碎花式的花纹,院子里的海棠落尽,时间在她的生命里展现出的单薄和匮乏逐渐使她的轮廓愈发清晰。一段对话结束,她看着窗外拔地而起的新式楼房,才一个月不到时间,迅速建立,周围陌生的环境,她并不熟悉,瓷砖冰冷的地面,狭小的书房,暗黄色的灯光,脆弱的对话,屋子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低沉和悲呛,她未曾醒觉,一时间感到孤独,窗外的建筑陷入沉寂,她隐隐的觉察到胃在疼痛,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她忽然发现眼泪的咸涩是她之前从未体会过的滋味。 十八年前,她初到上海,小小的手被外婆紧紧拽着,一路的长途汽车加上十数小时的绿皮火车,临行前,她和外婆与表妹居住在县城的一个小旅馆里,公共的浴室,湿滑的地面,散发的热气混合滚烫的水泥地,她蜷缩在单人的木板床上,床发出刺耳的声响,门外时不时有路过的人,她的眼前出现一副陌生的画面,陌生的男子与她时而熟悉的成年女子出现在一起,成年女子留着短发穿着时下新潮的衣服,带着她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她的世界被一种外来的力量蓄意安排,她无所抗拒,唯有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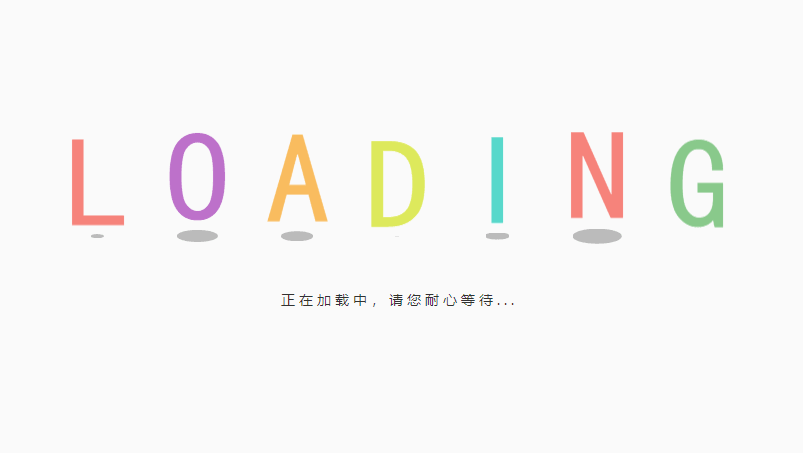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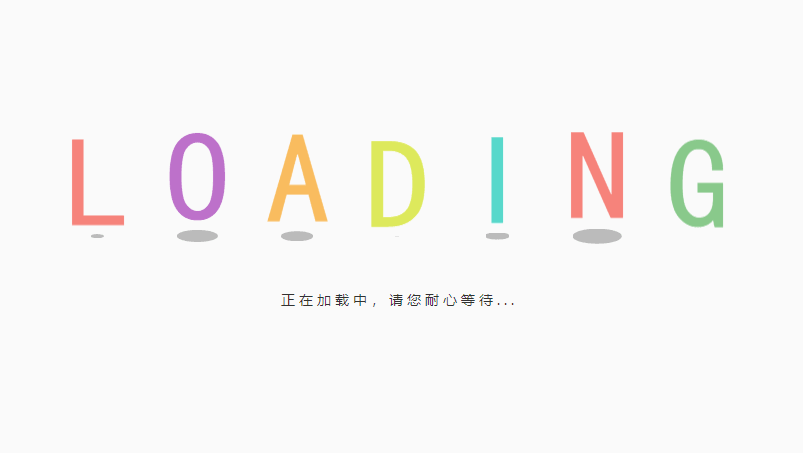 衢州夏季的火车站外,几个卖炒粉和饮料的摊贩依次林立,她穿着一条白色碎花的裙子,指了指面前的一个摊贩对外婆说她饿了,外婆给她买下食物后进入火车站排队,候车室封闭的空间,混合着汗液、酸臭,泡面的气味,交织在一起。 人因为贫穷而不得不选择顺从,卑微低廉的收入和日渐堆积的欲望难以平衡,她感受过贫穷带来的困顿与绝望,高烧不退,外婆口袋里的钱微薄,无力支撑医药费,她躺在床上一直休息,眼泪时而流下,她想念母亲,带走她,身边的人小声低吟,她在梦境迷糊之间看到一辆列车行驶在大雪覆盖的雪地上,她看着列车一直行驶,她在追赶,最终她看见列车停下,只是前面并无延伸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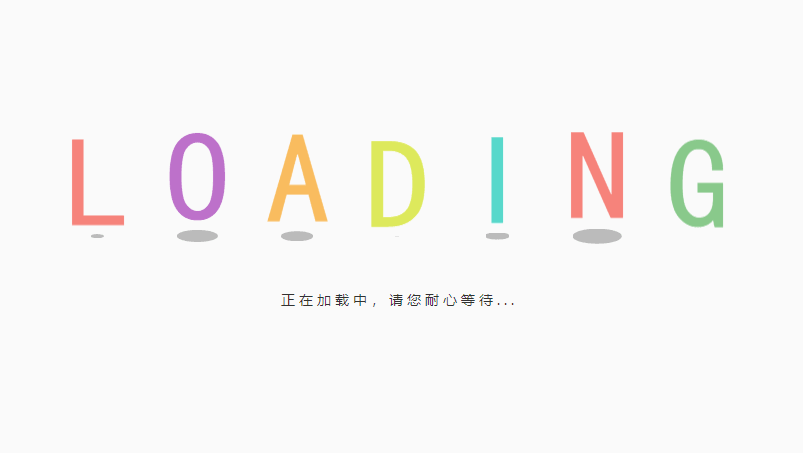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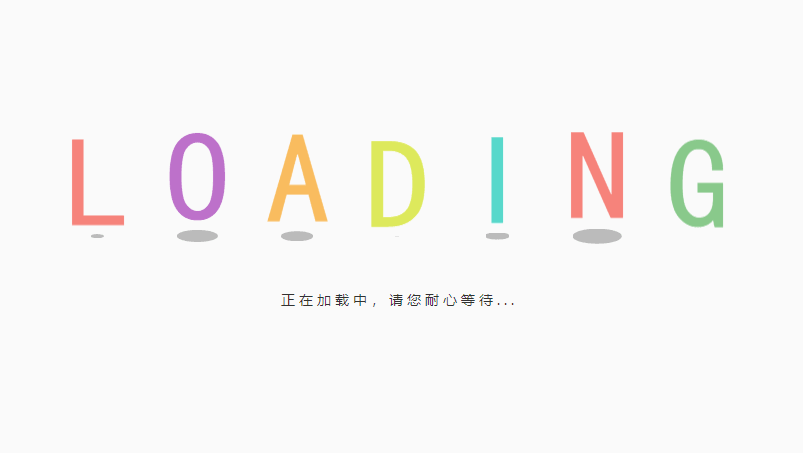 火车外暮色凝重,铁轨在缓慢行驶,这样的绿皮车在今天,她已经很少乘坐,唯一的一次是在2019年时,她坐长途的火车去往西安,一夜未眠。社会比她所想的要残酷,十来个面试官,她拖着紧张疲惫的精神坐在她们面前,感到压力和彷徨,她早已预感,结局就在眼前,她有过幻想和期许,直到破碎时,她才发现她比她想的还要脆弱。 漫长旅途,他陪伴她,陌生环境让她感到安心。小镇里,人群褪去,灯光熹微,星河在沙漠上空闪烁,她喝下半斤青稞酒,酒精的力量使她感到愉悦,心情释放,她渴望能在这里生活下去,拥有一个孩子,过着平凡的生活。 秋雨带来的寒意陡增,南方天气湿润,她决定外出,白日醒来时,眼泪已经干涸,她顺手翻阅身旁的书籍,庆山的短篇小说,她看着这位女作家的文字在数年里发生的变化,心境成熟到坦然,但世俗观念里仍旧有和现实不符合的地方,这是她唯一不喜欢她的介质。她倾向不断付出和收获,尽管她时常感到疲累。 县城里的步行街,她跟在身后,一言不发,望着她的背影,她想起童年时背着她的那个女子,坚韧顽强,如今容颜老去,精力不再,所渴望的和期盼的她难以维系,身陷艰难与犹豫之间,她看到她心底的力量,精神仍然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柱。眼前的男子并非她所爱,这半生里的追求已经到了迟暮之时,她很少在反驳,有时沉默,不再有冲突,她们划分,两个不同的世界,应该有交集,言语中依然听见责怪,是过往无数争吵带来的破碎、无奈。 她对着镜子,看到镜子中苍白的自己,短发,红色毛衣,白色棉服外套,她依旧觉得寒冷。傍晚时,她感到疲惫,在母亲的床角边上沉沉睡去,十几分钟里她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醒来时的一刹那,她仿佛回到了过去,长发落肩,白灰色校服,在母亲放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中不情愿醒来,刷完牙坐在母亲写字台前的桌子上照镜子,给自己拍照,少女青涩的容颜和叛逆,是她十六岁生命里最鲜明的色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