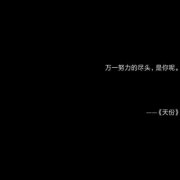满特嘎
|
满特嘎是我堂姐阿拉它的丈夫。第一次来赤峰是接阿拉它和儿子双山。我大伯的女儿们,在孩子生到我妈感到气愤的程度时,就被招到赤峰做绝育手术并调养一个阶段。阿拉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手术,于是愉快地在这里度假,她尽一切能力把我们家擦的擦、洗的洗,总之,一切都是亮堂堂的。我爸常夸阿拉它漂亮:“这孩子当电影演员都行。” 阿拉它的长相的确很好看。一笑,便有喜气洋洋的样子,演员也不一定如此。只有从心底笑,才好看,像花朵在早晨遇到阳光时一样。阿拉它在我家头几天还很快乐,到处笑。后来渐渐沉默,她抱着双山倚在门框小声唱歌。那些歌在我听来一律是忧伤的。她一边唱,一边用手轻轻拍着双山的背。双山才几个月,脑袋大到仿佛脖子都撑不住,晃着。而我父母下班之后,阿拉它麻溜儿干活,不唱了,也不怎么笑。我妈说:“给满特嘎写信了,接你。”阿拉它脸“忽”地红了,抱儿子转过身。那时我虽然还小,但能从阿拉它的眼睛里看出她在思念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如果目光变得遥远,并常常失神,大约就是这样吧。 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浓重的膻味熏醒,睁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他就是满特嘎。这个人的脸像树皮一样粗糙,颜色深红,眼睛细长,前额的抬头纹仿佛是被沉重之物压出来的。这张脸和阿拉它白净的、如满月般的笑脸并列在一起,实在太有趣了。按城里人的眼光看,也不般配。满特嘎向我笑一下,仿佛很吃力,旋即闭上了嘴。我为阿拉它感到惋惜,并对她的神色飞扬有些不满。膻味是满特嘎扛来的羊肉上带来的,还有炒米、奶酪。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一家人过春节所享用的美味。 满特嘎来了之后,阿拉它一往情深地望着他笑。如果撕一角报纸放到满特嘎脸上,会立刻被阿拉它的目光所点燃。隔一会儿,她就把双山递到他怀里,然后看他俯视儿子的样子再笑。而满特嘎是腼腆的,被阿拉它注视久了,就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顺势连胡子带嘴捋一把。他看儿子的表情是怜悯的,看我父母的目光非常恭顺,而看阿拉它时,在细长眼睛的深处,跳荡着男人的柔情。无疑,阿拉它了解并幸福地享用着这种眼神。 晚饭前,满特嘎轻巧地咬下酒瓶的铁盖,像咬一块胶皮。斟上酒,双膝跪地,站起再躬身,把酒举过头顶,献给我爸。我爸接过酒一饮而尽的时候,满特嘎出神注视,仿佛很感动,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话来。事实上,满特嘎几乎不言语,话都挤在脸上,在粗糙的眉眼间似更生动。 我现在算起来,满特嘎和阿拉它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吧。我今年去看他们的时候,堂姐老了,满特嘎还是那个样子,但头发已经雪白。他头发卷曲,像戴一顶羊羔皮的帽子一样,五分硬币似的小卷儿闪闪泛着银光,使绛紫的脸膛笼罩安详之气。阿拉它说,大儿子结婚了,意谓他们已经为之盖房娶亲了,只剩下双山。双山已经高中毕业,文静地听我们谈话。 在科尔沁草原上,积十几年劳动所得,才勉强为一个儿子完婚,而另一个儿子的婚事就意味着阿拉它和满特嘎必须要努力到生命的终点,而他们把此事视为一种光荣的职责。我感到,在满特嘎心里,一切思想都没有了,不妨做一棵树。他的思想都被我堂姐移植走了。他们的思想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活着,并且让孩子们更好地活着。 |